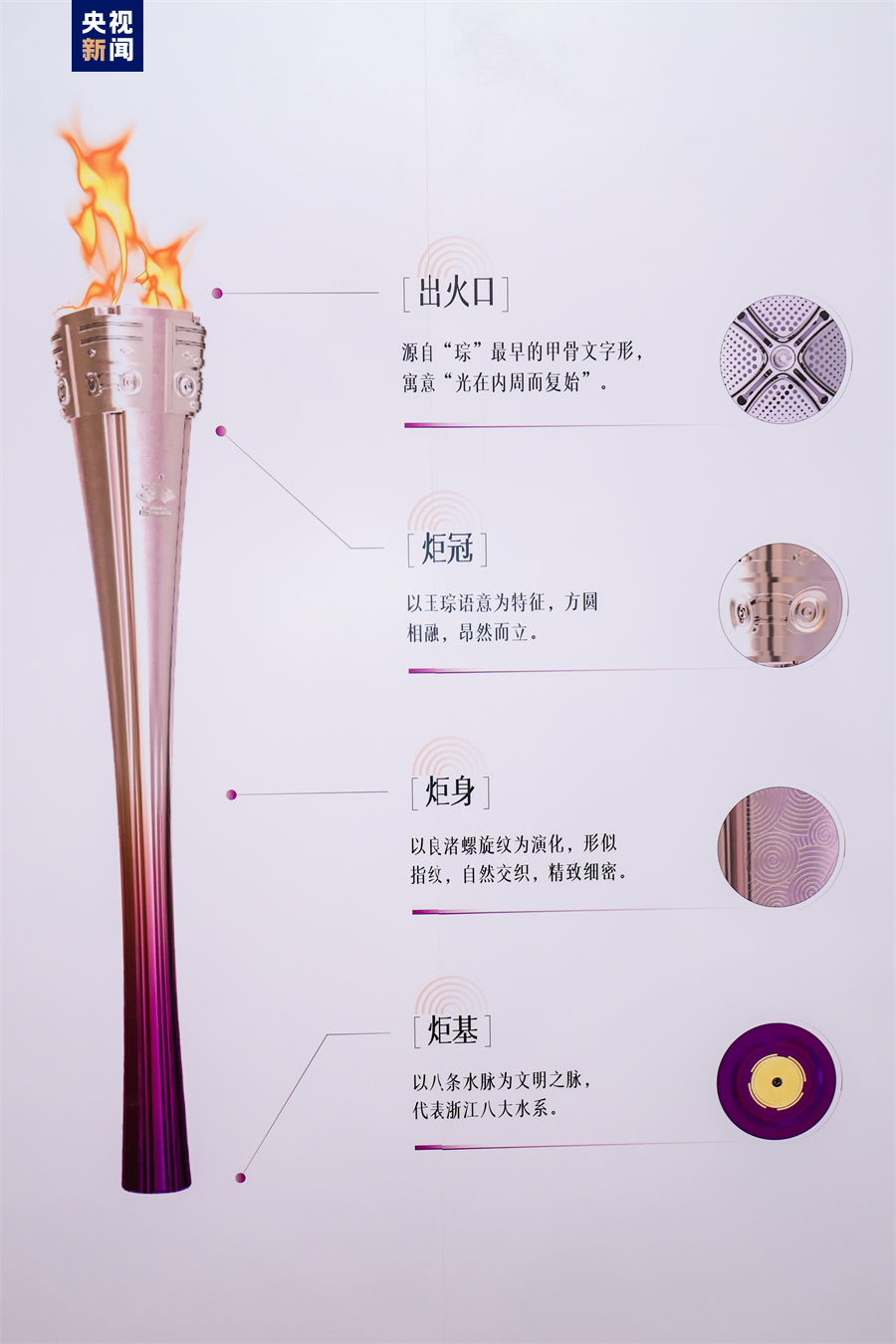卡羅維發(fā)利國(guó)際電影節(jié)獎(jiǎng)杯(第55屆卡羅維發(fā)利國(guó)際電影節(jié))
【文/觀察者網(wǎng)專欄作者 聆雨子】
一
2020年2月9日,好萊塢杜比劇院,第92屆奧斯卡頒獎(jiǎng)典禮,在宣布”最佳國(guó)際電影”(也就是通常所說(shuō)的“最佳外語(yǔ)片”)之前,現(xiàn)場(chǎng)特意播放了一段經(jīng)典作品集錦,其中,有一部被美國(guó)人視為巔峰之作的華語(yǔ)電影,它的名字叫《英雄》。
《英雄》的導(dǎo)演,是張藝謀。
2017年2月26日,好萊塢杜比劇院,第89屆奧斯卡頒獎(jiǎng)典禮。主持人按慣例調(diào)侃在座的一眾大牌明星,說(shuō)到馬特·達(dá)蒙:“他本可以主演《海邊的曼徹斯特》,卻把這個(gè)角色給了凱西·阿弗萊克,自己出演了一部令人呵呵的中國(guó)電影,虧損達(dá)八千萬(wàn)美元之巨”。話音未落,現(xiàn)場(chǎng)一片會(huì)心哄笑。這部“令人呵呵”的中國(guó)電影叫《長(zhǎng)城》。
《長(zhǎng)城》的導(dǎo)演,也是張藝謀。
一次敬意,一次嘲弄,不過(guò),無(wú)論哪次,當(dāng)事人都不在場(chǎng)。
他在的那回已是十七年前,也就是《英雄》獲提名的那年。那年最佳外語(yǔ)片花落德國(guó)的《何處是我家》,在場(chǎng)的他,沒(méi)聽(tīng)到自己的名字。
當(dāng)時(shí)他一定沒(méi)想到,他與奧斯卡的故事幾乎到此結(jié)束,而奧斯卡再想起他,是以上述兩種方式。

張藝謀(資料圖/SONY PICTURE CLASSICS)
《英雄》在美國(guó)一度被視為神作,《時(shí)代周刊》將之選為“2004全球十佳電影”。可在國(guó)內(nèi)它遭遇口誅筆伐,從故事單薄、色彩虛浮,到歷史觀爭(zhēng)議,盛名之下,冷嘲熱諷。
但那時(shí)的張藝謀不在乎,因?yàn)樗木褪乔罢撸踔量梢哉f(shuō),他拍攝《英雄》的唯一動(dòng)機(jī),就是用它去追逐那個(gè)叫奧斯卡的東西。畢竟,國(guó)內(nèi)他封圣多年,歐洲三大電影節(jié)也被他收割了無(wú)數(shù)光榮,只有奧斯卡,成了唯一沒(méi)“染指”的目標(biāo)。
那之前,已有過(guò)若干次近在咫尺,當(dāng)然也就有若干次失之交臂:
1990年張藝謀憑《菊豆》獲最佳外語(yǔ)片提名,1991年張藝謀憑《大紅燈籠高高掛》獲最佳外語(yǔ)片提名,1993年陳凱歌憑《霸王別姬》獲最佳外語(yǔ)片提名,1993年顧長(zhǎng)衛(wèi)憑《霸王別姬》獲最佳攝影獎(jiǎng)提名。
他們?cè)?jīng)遭遇的批評(píng)和詬病:后殖民主義美學(xué)、自我奇觀化、熱衷拍攝本民族最落后與丑陋的東西去討好西方……都與他們的奧斯卡情結(jié)有關(guān)。
他們后來(lái)遭遇的批評(píng)和詬病:視覺(jué)空間侵占了思想空間,生硬地堆砌色塊和元素,光鮮的感官刺激背后人文關(guān)懷盡失……還是與他們的奧斯卡情結(jié)有關(guān)。
這次給他靈感的人叫李安,學(xué)貫中西的華裔導(dǎo)演,剛憑借《臥虎藏龍》斬獲滿堂彩、將最佳外語(yǔ)片收入囊中。
他好像一下子觸類旁通,明白了美國(guó)人喜歡什么。于是他以《臥虎藏龍》為參照,配上自家絕學(xué),研發(fā)出一種叫做“中式古裝大片”的東西,并且一條道走到黑:接下來(lái)還會(huì)有《十面埋伏》和《滿城盡帶黃金甲》,當(dāng)然,那倆,連提名都沒(méi)摸著。
和他一起陷入魔咒的,還有他的同輩兄弟們(在中國(guó)電影史敘述中,他們被喚作“第五代”)——陳凱歌的《無(wú)極》、馮小剛的《夜宴》,仿佛認(rèn)準(zhǔn)這是比佛利山莊的評(píng)委們吃定了的美學(xué)解碼器,結(jié)果卻是,口碑一部比一部崩壞。
仿佛久坐替補(bǔ)席的二線隊(duì)員,心心念念都在登場(chǎng)機(jī)會(huì)上,至于那是誰(shuí)的主場(chǎng)?規(guī)則由誰(shuí)制定?自己的技術(shù)特點(diǎn)是什么?上了場(chǎng)該扮演什么角色?不上場(chǎng)又會(huì)怎樣?這些問(wèn)題,倒是從來(lái)沒(méi)想清楚。
李安終究比“第五代”更懂美國(guó)人:當(dāng)玉嬌龍和李慕白站在兩片竹葉上飛舞著比劍,老美們發(fā)自肺腑地如癡如醉,可當(dāng)甄子丹和梁朝偉在酒館里伴著琴聲和雨聲進(jìn)行“意念對(duì)決”,他們就只剩莫名其妙。
說(shuō)白了,美國(guó)人能遠(yuǎn)觀東方美學(xué),卻走不進(jìn)東方哲學(xué)和玄學(xué)。
這個(gè)屢敗屢戰(zhàn)屢戰(zhàn)屢敗的悲壯故事,不僅屬于張藝謀自己,也是他所代表的全體中國(guó)影人,在一個(gè)相當(dāng)漫長(zhǎng)的歷史時(shí)區(qū)內(nèi),對(duì)奧斯卡百折不撓的饑渴態(tài)度——想當(dāng)然地將之視為電影界的至高榮譽(yù),以獲得它的垂青作為職業(yè)生涯的最高肯定,以它的口味喜好(往往還是一廂情愿揣測(cè)出的)作為創(chuàng)作風(fēng)格的指南配方。
信念可嘉、勇氣可感,卻忽略了一個(gè)顯而易見(jiàn)的謬誤:奧斯卡的全稱是“美國(guó)電影藝術(shù)與科學(xué)學(xué)院獎(jiǎng)”,而不是“世界電影最佳優(yōu)勝獎(jiǎng)”。
嚴(yán)格意義上,它只是一個(gè)由本土科研機(jī)構(gòu)作為學(xué)術(shù)支撐的、屬于某個(gè)國(guó)家內(nèi)部的獎(jiǎng)項(xiàng)評(píng)比(當(dāng)然,它的準(zhǔn)入機(jī)制放得比較寬,愿意把所有曾在該國(guó)公映的電影納入擇選視野)——就像戛納、柏林以及威尼斯(這仨好歹還有個(gè)“國(guó)際”電影節(jié)的頭銜),就像蒙特利爾、卡羅維發(fā)利或者圣丹斯,就像金球、金像、金馬,就像金雞百花。
沒(méi)人規(guī)定過(guò),它是“電影界的至高榮譽(yù)”。
所以,你一邊認(rèn)定它代表了世界,一邊又苦于美國(guó)人看不懂自己,殊不知,“美國(guó)人看不懂的”,也是世界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是,更大更真實(shí)的那部分。
二
1927年它作為一尊獎(jiǎng)杯和雕塑被設(shè)計(jì)完成,1928年它作為一種制度和程序被確立與認(rèn)可,1929年它作為一個(gè)典禮和盛會(huì)而首次舉行;它起自一戰(zhàn)之后世界藝術(shù)的普遍低潮期,它作為契機(jī)開(kāi)啟了好萊塢第一個(gè)黃金時(shí)代,它伴生和見(jiàn)證了幾乎整一部人類電影的發(fā)展史。
你說(shuō)它集專業(yè)性、公正性、商業(yè)性于一身,你說(shuō)它佳作等身、賓客盈門、俊男靚女、鮮花掌聲,你說(shuō)它有票房與資本滾雪球般的增長(zhǎng)速度,有業(yè)內(nèi)交口稱贊的信譽(yù)和口碑,可這些,不是世界上任何主流藝術(shù)獎(jiǎng)項(xiàng)維持運(yùn)行的共享價(jià)值?
那為什么偏偏是它?
還是李安的玩笑話一針見(jiàn)血:“說(shuō)白了,奧斯卡完全就是一宗大買賣。”
當(dāng)文化產(chǎn)業(yè)化和商品化,在資本跨國(guó)流動(dòng)中成為新的普世價(jià)值;當(dāng)大眾傳媒和視聽(tīng)藝術(shù),不斷重塑著人類對(duì)宇宙和自身的想象;當(dāng)電影工業(yè)造就了一種審美范式和樣板,習(xí)慣于為麻木不仁的時(shí)代定制興奮點(diǎn)。奧斯卡作為全球電影最集中、最富代表性的環(huán)節(jié),責(zé)無(wú)旁貸地站在前臺(tái),來(lái)引導(dǎo)和象征這場(chǎng)光怪陸離的娛樂(lè)游戲,讓一切熾熱和躁動(dòng)有章可循:
仿佛,誰(shuí)能揣度它的圣意、摸準(zhǔn)它的脾性、獲得它的垂憐,就意味著,誰(shuí)將迅速被頂級(jí)財(cái)富的圓桌會(huì)所接納和認(rèn)可。
它的近旁,是好萊塢精密無(wú)匹的運(yùn)作模式、縱貫四海的發(fā)行渠道、富可敵國(guó)的資本保障,是手握重金的片廠和制作公司,它們放眼量、廣撒網(wǎng),依賴于奧斯卡這個(gè)冠冕堂皇的認(rèn)證標(biāo)準(zhǔn),在一片嗷嗷待哺的扶植對(duì)象里,為自己找到最佳目標(biāo),然后師出有名地迅速聚攏資源和流量。
它的身后,是無(wú)數(shù)需要選題的媒體,和需要談資的普通人,是等著新的成功者的名利場(chǎng),和期盼新的愛(ài)豆的粉絲團(tuán),是站在影院售票處、DVD貨架、視頻網(wǎng)站和蘋(píng)果下載排行榜前無(wú)所適從的觀眾,他們正等著奧斯卡這張“觀影世界的導(dǎo)游圖”制作完成,為自己破解選擇恐懼癥,在想象中重歸藝術(shù)品位的最前沿,在社交網(wǎng)站的自我簡(jiǎn)介上,心安理得地掛上“電影發(fā)燒友”的標(biāo)簽。
等待獲得成功者、等待培植成功者、等待見(jiàn)證成功者,達(dá)成了心照不宣而又堅(jiān)不可破的盟約。
換句話說(shuō),當(dāng)大多數(shù)評(píng)獎(jiǎng)活動(dòng)尚停留在“能慧眼識(shí)珠地選拔和表彰一批好作品”的時(shí)候,奧斯卡已經(jīng)順利上位、把自己鍛塑為“好作品”的同位語(yǔ)。
于是,一種度量衡上的置換,悄然發(fā)生了:奧斯卡成為評(píng)估影片的一個(gè)慣常尺度和標(biāo)桿,成為一種習(xí)慣性用語(yǔ)和一種新的褒意詞匯——不再是“這部影片很好,所以它應(yīng)該獲得奧斯卡”,而是“這部影片獲得了奧斯卡,所以它肯定很好”;不再是“因?yàn)橛屑炎鳎砸袏W斯卡來(lái)發(fā)現(xiàn)和推廣它們”,而是“因?yàn)橛袏W斯卡,所以我們總該去找到和拍出一些奧斯卡標(biāo)準(zhǔn)的電影”。
然后,小金人背后所表征的好萊塢文化模式和美國(guó)價(jià)值,更有理由翻手為云覆手為雨,它們幾乎在每一部奧斯卡獲獎(jiǎng)影片中得到一輪新的固化:英雄主義與人道主義雙向互動(dòng)的國(guó)家精神,強(qiáng)調(diào)傳統(tǒng)與和解的中產(chǎn)階級(jí)審美趣味,安全,主流,反戰(zhàn),反歧視。
都說(shuō)美國(guó)人用“三個(gè)片”統(tǒng)治世界:芯片(科技)、膠片(文化)、薯片(生活方式)。奧斯卡依賴于不斷進(jìn)化的芯片,奧斯卡裝裹了足夠誘人的薯片,奧斯卡就是膠片本身。
三
當(dāng)然,奧斯卡也有自己的執(zhí)念:那就是,不斷向所有人證明,它首先是“學(xué)院獎(jiǎng)”,而不僅僅是“大買賣”。
一方面,它總竭力與“商業(yè)性”這幾個(gè)在評(píng)獎(jiǎng)季里不受歡迎的字眼劃清界限:
馬修·麥康納(《達(dá)拉斯買家俱樂(lè)部》)、查理茲·塞隆(《女魔頭》)、埃迪·雷德梅恩(《萬(wàn)物理論》)、安妮·海瑟薇(《悲慘世界》)、還有我們敬愛(ài)的小李子(《荒野獵人》),都在主動(dòng)褪去俊男靚女的偶像光環(huán)、主動(dòng)自毀、主動(dòng)扮丑之后才折桂蟾宮;
幾乎每年全球票房10強(qiáng)的大體量巨片,都會(huì)無(wú)一例外地被拒之門外,蝙蝠俠蜘蛛俠哥斯拉金剛組團(tuán)來(lái)犯,也摸不到主要獎(jiǎng)項(xiàng)的邊緣——當(dāng)年《阿凡達(dá)》的北美票房幾乎是《拆彈部隊(duì)》的60倍,卡梅隆仍然只能在前妻畢格羅面前折戟投降。
凱瑟琳·畢格羅憑《拆彈部隊(duì)》成首位奧斯卡最佳女導(dǎo)演(資料圖/Pinterest)
而那些金牌選手,更像一些四平八穩(wěn)的好學(xué)生:成績(jī)出眾,品德高尚,不觸碰極端問(wèn)題的紅線,又帶著一點(diǎn)看起來(lái)很濃厚的人文情懷,既非生澀叛逆的小眾文藝,也不顯得胸大無(wú)腦。
至于索尼、華納、派拉蒙、福克斯、夢(mèng)工廠的大老板們,也不會(huì)過(guò)分寂寞,因?yàn)檫€有一堆最佳音效最佳視效最佳剪輯最佳攝影最佳服裝設(shè)計(jì)的技術(shù)類獎(jiǎng)項(xiàng),等著他們的超能英雄和外星怪獸,去坐地分贓。
最終,奧斯卡又在縫縫補(bǔ)補(bǔ)中,鋪開(kāi)了一個(gè)皆大歡喜的好局面。
另一方面,它依然在每個(gè)細(xì)節(jié)里宣告自己的海納百川、天下來(lái)同。
你會(huì)發(fā)現(xiàn),這幾年的奧斯卡得主,越來(lái)越講究美國(guó)式的“政治正確”:《綠皮書(shū)》講的是跨越膚色和階級(jí)的友誼,《水形物語(yǔ)》講的是跨越物種的愛(ài)情童話,《月光男孩》講的是跨越性別的自我尋找與發(fā)現(xiàn)。
共同點(diǎn)與公約數(shù)一目了然:它們都很“白左”——平等、博愛(ài)、對(duì)不同種族的包容。那是美國(guó)人,或者說(shuō)整個(gè)西方社會(huì),為自己早早總結(jié)出的,“我們憑什么引領(lǐng)世界”的答案。
眾所周知,西方這幾年問(wèn)題和麻煩太多:從英國(guó)脫歐到德法一連串恐怖襲擊,從移民危機(jī)到反種族歧視示威,從美國(guó)政府停擺到國(guó)會(huì)大廈被占領(lǐng),更勿論新冠疫情面前的低效表現(xiàn)。所以,那些他們信仰了幾百年的東西、他們認(rèn)定這是自己稱雄世界之理由的東西,正在前所未有地遭遇沖擊。
這時(shí)候,他們需要的不是懷疑、討論、剖析,而是重新不由分說(shuō)地讓自己去樹(shù)立和相信,哪怕是,“騙”自己去樹(shù)立和相信。
這個(gè)過(guò)程里,奧斯卡責(zé)無(wú)旁貸。
至于它落到現(xiàn)實(shí)中能產(chǎn)生多少實(shí)際作用,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畢竟,弗洛伊德慘死之前,《為奴十二年》、《幫助》、《白宮管家》、《珍愛(ài)》這些關(guān)于“有色人種的夢(mèng)想與尊嚴(yán)”的電影,全都在奧斯卡贏得盆滿缽滿。
露皮塔·尼永奧借《為奴十二年》獲得奧斯卡最佳女配角
“海納百川”的終極表現(xiàn),就是去年那個(gè)出人意料的結(jié)果:韓國(guó)的《寄生蟲(chóng)》大獲全勝——它肯定不是奉俊昊最好的電影,更不是韓國(guó)最好的電影,但它太吻合奧斯卡此時(shí)此地的需要。
它就像是,奧斯卡給自己下的一劑猛藥。
四
今年的張藝謀,非常非常淡定,去年他的《一秒鐘》平穩(wěn)破億,今年他的新片《懸崖之上》行將上映——懸疑諜戰(zhàn)商業(yè)大制作,怎么看也不是奧斯卡會(huì)偏愛(ài)的品相,當(dāng)然,他不會(huì)care了,因?yàn)檎l(shuí)都看得出來(lái),奧斯卡已經(jīng)從他的藍(lán)圖里,退行消泯。
接下來(lái)他還會(huì)有《堅(jiān)如磐石》和《手》等著上映,它們都指向國(guó)內(nèi)市場(chǎng)、也只關(guān)心國(guó)內(nèi)市場(chǎng)。
更何況,張藝謀這幾年最大的工作重心,毫無(wú)疑問(wèn)是北京冬奧會(huì)的開(kāi)閉幕式——相比奧斯卡這樣的“美國(guó)內(nèi)部獎(jiǎng)項(xiàng)”,那才是更無(wú)爭(zhēng)議的世界性活動(dòng)、全人類盛事。
2020年,中國(guó)電影全年票房204.17億元(約合31億美元),正式超過(guò)北美(21億美元),成為全球第一大票倉(cāng)。
2021年春節(jié)檔,國(guó)內(nèi)電影票房超過(guò)78億元,比2019年同期增長(zhǎng)32%,這還是在影院上座率有所限制的情況下。
近兩年里,除了個(gè)別超級(jí)IP(比如《復(fù)仇者聯(lián)盟》),《終結(jié)者:黑暗命運(yùn)》、《決戰(zhàn)中途島》、《雙子殺手》、《沉睡魔咒2》、《信條》、《花木蘭》、《怪物獵人》等好萊塢重頭戲,幾乎無(wú)一例外地在中國(guó)內(nèi)地遇冷,爆款變成了《戰(zhàn)狼2》、《紅海行動(dòng)》、《我不是藥神》、《流浪地球》與《你好,李煥英》。
當(dāng)你發(fā)現(xiàn)身邊就有一條前途光明的賽道,又何苦去上趕著、吃力不討好地追逐人家制訂的規(guī)則?
這個(gè)走出焦慮和破除迷信的故事,同樣不僅屬于張藝謀自己,這是他所代表的全體中國(guó)影人,在一個(gè)嶄新的歷史時(shí)區(qū)內(nèi),從遷就與迎合,走向理性與客觀的步履堅(jiān)定。
歸根結(jié)底:奧斯卡的“祛魅”背后,是中國(guó)文化自信的“返魅”。
當(dāng)然,回歸一顆平常心的話,奧斯卡還是一塊可供參照的他山之石:拋開(kāi)價(jià)值觀和文化輸出不提,所有勝出者,還是擁有一些最簡(jiǎn)單不過(guò)的優(yōu)點(diǎn)——踏踏實(shí)實(shí)地?cái)⑹銮楣?jié)、勤勤懇懇地運(yùn)用技術(shù)、認(rèn)認(rèn)真真地討論道理。
這再簡(jiǎn)單不過(guò)的幾句話,已經(jīng)足以構(gòu)成電影藝術(shù)最本質(zhì)的公理。
只不過(guò),這些公理,不一定要用來(lái)講一個(gè)美國(guó)人喜歡、并且愿意發(fā)獎(jiǎng)給你的故事,它們同樣可以適用于我們的故事、適用于“講好中國(guó)故事”。
本文系觀察者網(wǎng)獨(dú)家稿件,文章內(nèi)容純屬作者個(gè)人觀點(diǎn),不代表平臺(tái)觀點(diǎn),未經(jīng)授權(quán),不得轉(zhuǎn)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zé)任。關(guān)注觀察者網(wǎng)微信guanchacn,每日閱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