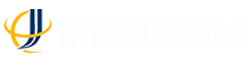廣西“砍手黨村”今昔:年輕人紛紛外出 依舊貧窮
楊成康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是主持修了一條從屯里到小學(xué)的路,將孩子們的上學(xué)路程縮短了30分鐘。他還把讀中學(xué)的女兒送到縣里,租房,偶爾陪讀,無論如何都要讓她讀個好學(xué)校。
對此,溫江村村民評價說,楊成康進(jìn)了監(jiān)獄,就像“讀了個大學(xué)”一樣長了見識。人們選他當(dāng)了屯長。
在距離中越兩國邊境只有30公里的廣西天等縣上映鄉(xiāng)溫江村,楊成康從過去到現(xiàn)在都是風(fēng)云人物。很少有一個群山環(huán)抱中的中國貧困村能像溫江村這樣引人矚目。12年前,這個村子的19個年輕人在深圳制造了一起搶劫案,手持砍刀把一位受害者的右手砍了下來,僅僅是為了搶走一部手機(jī)。隨后,溫江村的秘密被發(fā)現(xiàn)了:當(dāng)時村里的四五百名年輕人中,有100多人在做這樣的“砍手黨”,重復(fù)著輟學(xué)、打工、辭工、團(tuán)伙搶劫的底層生存路徑。溫江村因此被冠之以“砍手黨村”的名號。
楊成康則是核心人物之一。當(dāng)年,他留著香港古惑仔電影人物“陳浩南”式的長發(fā),在被判刑8年之前,一直被視為多謀善斷、意氣風(fēng)發(fā)的“砍手黨”重要人物。
如今,這段歷史都刻在了他的身體上。他外表粗糙,鼻寬唇厚,長發(fā)已改為平頭,毫不引人注意。“砍手黨”并不光彩的過去也真的砍下了他的手指:他的手掌粗壯,只是一只手的大拇指沒有了,另一只手上有兩道明顯的刀疤。過去的印記還隱藏在兩只腳上,一只被完全挑斷腳筋,另一只連著一些。
這些是在一次江湖爭奪戰(zhàn)中被對手砍斷的。他的右大腿上有一個條形疤,是17歲時在村里幫人打群架,被對方用砂槍轟傷的;左邊大腿也有一處槍傷,那是1999年拒捕時,被警察射中的。
10多年過去了,在廣東服刑8年的楊成康已出獄回到村里,而昔日的“砍手黨村”卻更加寂靜,重復(fù)著日益衰敗的農(nóng)村日常——搶劫從未給它帶來真正的財富。
從縣城到溫江是一趟漫長而令人眩暈的旅途。汽車在山與山之間繞來繞去,窗外的景色優(yōu)美而寂寥。
“如果石頭能賣錢,那我們肯定發(fā)財了。”當(dāng)?shù)厝诵ΨQ,家鄉(xiāng)一無所有,除了連綿不斷的青山。山巒和貧窮從不同維度包裹著溫江村,把它圍得死死的,10個屯散落在河谷間,寂靜無聲。村里的老人與小孩普遍最遠(yuǎn)只到過縣城。在他們的大腦中,越南與省內(nèi)的桂林、首都北京一樣遙不可及。年輕人則散落在廣東各個城市的工廠里,他們不斷變換工作,卻從未真正走進(jìn)腳下的城。
多年以來,貧窮如溫江村的地貌一樣沒有什么變化。這里的村路上堆疊著不同動物的糞便。因?yàn)槿卞X,村子里大多數(shù)房屋紅磚外露,窗戶的位置留著一個洞,沒有玻璃窗。雖然沒錢給房子刷石灰、鑲瓷磚,但家家戶戶都修了通往二樓的樓梯,等著哪天發(fā)跡了蓋一棟“高樓”。房屋的高度是財富和地位的象征,一戶人家因?yàn)樾蘖?層高的房子而成為全村最讓人羨慕的家庭。
無論過去,還是現(xiàn)在,為了建一棟足夠高的房子,村里的年輕人紛紛外出打工。有人算了一筆賬:在縣城里做工一個月最多賺一兩千元;到了廣東則起碼有四五千元。當(dāng)?shù)貙倏λ固氐孛玻讳z頭挖下去就是厚厚的巖石,收成不好。種地已是年輕人不會考慮的選項(xiàng),他們絕不會把未來賭在農(nóng)田里,田間地頭只留了些年邁的身影,和他們彎成90度的腰。
即便在最炎熱的夏天,少了年輕人的村莊還是顯得蕭瑟無比。衰老的氣息在早晨9點(diǎn)的陽光里漂浮著、下墜著。
馮成金獨(dú)自坐在門口的板凳上,衣服很難辨認(rèn)出初始的顏色,腋下和口袋處都破了洞,他時不時從嘴里吐一口口水到地上,腳下積了一灘,把土地染成深色。這位64歲的老人已經(jīng)在這里坐了3個小時,還將像這樣繼續(xù)坐上一整天。一天過去后,他只是追隨著太陽,把板凳從一邊移向了另一邊。
他身后的房子,是一生的榮耀。溫江村很少有人家能夠在空曠的房子里擺上家具,馮成金家卻有一套沙發(fā),沙發(fā)后面掛著一個“電腦數(shù)碼信息歷”,其實(shí)是一副掛歷畫,下面顯示年月日和時間,畫上有彩虹、向日葵、別墅和一輛法拉利跑車,最上方寫了四個大字:幸福家園。
馮成金艱難地挪動著步子——因?yàn)橹酗L(fēng),他只有半邊身子能動,說話已不太清晰了——為這幅畫通了電,“幸福家園”立馬亮了起來,底下的日期也跟著閃爍,只是還停留在公元2010年。
那時,他還是溫江村的支書,“說話聲音大,吃得穿得都比我們好。”現(xiàn)任支書的兒子趙文學(xué)說,“他成天穿著西裝,我們連衣服都沒有。”
那時,馮成金的家里有個鐵盒子,里面裝著厚厚的一沓緝查通知書,他對前來采訪“砍手黨村”的記者感慨:“這些小伙子,在家好好的,怎么一出去就變成壞人了呢?”他曾帶著記者一家家地拜訪犯罪嫌疑人的家,幾年之后,等到記者再來回訪,馮成金唯一的兒子因搶劫在廣東被抓,侄子也“進(jìn)去”了。甚至他親家的兒子也服刑去了。當(dāng)時的報道里,他自嘲,自己也成了服刑家屬的一員。
不過,到了2016年夏天,他坐在門口,吃力地克服中風(fēng)的種種癥狀,顫顫巍巍但又堅(jiān)定地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否認(rèn)了這些事情。他說,家里沒有人被抓進(jìn)去。
馮成金家的墻壁上留下了他人生的光彩時刻。10年前的照片上,他一頭油亮的黑色卷發(fā),穿著深藍(lán)色西裝,還歪歪扭扭系著紅色領(lǐng)帶,一張鄉(xiāng)人大代表會議的出席證端端正正地插在照片旁;另一張鑲了相框的照片上,他穿著西裝,背景是天安門廣場。這是PS的,溫江村很多人家的墻上,都有這樣一張主人站在天安門前的合成照。
馮家那些照片所環(huán)繞著的,是一張油膩膩的獎狀,外面裹了一層又一層透明膠,灰塵和油污讓它看上去臟極了,仔細(xì)辨認(rèn),才能看清那上面寫的字:馮成金同志在自衛(wèi)還擊保衛(wèi)邊疆戰(zhàn)斗中,機(jī)智勇敢,出色完成任務(wù),榮立三等功。
如今頭發(fā)花白、口齒已不伶俐的馮成金說,這張獎狀是這間屋子里最珍貴的東西,比得上兒子給買的新冰箱。
那個冰箱是掛著蜘蛛網(wǎng)的屋里唯一的亮色,雖然里面空空如也。馮成金有一兒一女,兒子早早就去廣東打工,帶著兒媳和兩個孫子,一年回來一次,女兒也早已嫁人。早些年有手機(jī),他還能跟兒子孫子聯(lián)系,現(xiàn)在,那部老式手機(jī)也不見了,紅磚上還留著粉筆記下的電話號碼。
說起這些,馮成金渾濁的眼睛里有淚流出,他哆哆嗦嗦的樣子,讓人分辨不出是出于傷心還是疾患。
馮成金的侄子參與的是2005年轟動一時的“少年阿星殺人事件”,因?yàn)楣ゅX糾紛,溫江人阿星刺死了廣東工廠的主管并搶走了400元錢,馮侄是同謀。當(dāng)時,用暴力來保障生存,在溫江村走出的打工者身上形成條件反射,他們本性不壞,但徘徊在善惡的邊緣。
阿星曾對采訪他的記者說:“我覺得城里人就是那個高樓,高到天上去了,我們在下面仰望,看得帽子都掉下來了,都看不到人家。”自身貧困但又被城市的富裕所誘惑,錢就成了他們的宗教。一位老鄉(xiāng)形容,搶到錢的那一刻會抬頭望著天空笑,不管明天死活。
在阿星的記憶里,跟風(fēng)搶劫一開始是無意識的,相互間的影響發(fā)生在同鄉(xiāng)間日常的交往中,那種交往是溫情脈脈,甚至是患難相助的。
阿星的本家長輩、溫江村村頭小賣店店主老閉說,阿星的父母現(xiàn)在還在廣東打工,他父親在2008年被工作多年的工廠辭退,從他出來打工的1992年,到被辭退的2008年,是中國經(jīng)濟(jì)增長的黃金時期,中國貨物出口額年增長率高達(dá)19.6%,制造業(yè)創(chuàng)造了中國GDP總量的1/3,“中國模式”引人關(guān)注。
如今,老閉并不清楚這家親戚的近況,說起那些犯人,很多留守的村民都搖頭不言,像村子里很多緊鎖的大門一樣諱莫如深。
老閉50多歲,個子不高,帶著3個孩子,開了家小賣部,出售5毛錢一袋的那類零食。
天空飄來一片烏云,群山很快變成了水墨色,四處游蕩的雞迅速排成一排躲在屋檐下。雨點(diǎn)打在磚瓦房和泥坯房上,寧靜的村莊只有動物的叫聲和流水潺潺,老閉家沒來得及封上的屋頂立刻噼里啪啦地漏起雨來。
“這房子是我老婆出去打工掙回來的錢,不是我哦。”老閉說,他3歲沒了母親,將近40歲才成家,“那時候年輕人談戀愛就是唱山歌,現(xiàn)在的歌節(jié)都是老人去,青年全部去廣東了。像大姐(即大女兒)那樣,要是讀書能夠認(rèn)懂,五六年之后再出去;要是考不上高中,就老老實(shí)實(shí)去打工,幫我們扛起這個家,不出去做工沒飯吃的。”如今,外出打工的溫江人不再做“砍手黨”。
他的大女兒今年14歲,一會和10歲的弟弟在小電視機(jī)前看碟片,一會跟12歲的妹妹在舊作業(yè)本上描圖案,聽到父親提到自己,抿著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下午3點(diǎn),一家人決定吃一天的第二頓飯,老閉炒了白菜,煮了一鍋稀飯,又拿出兩罐啤酒,遞給兒子一罐。
兒子吃完飯,無聊地坐在柜臺里逮蒼蠅,他馬上要讀小學(xué)五年級了,家的對面就是溫江小學(xué)。一名六年級的學(xué)生說,原來班上有48個人,現(xiàn)在只有23個了,很多同學(xué)都跟著父母去了廣東,回來之后變化很大,“變白了,變高了,穿的衣服好看,學(xué)習(xí)變得好好。”
那些隨著父母打工的孩子只回來幾天參加考試,就又匆匆離開。這所擁有6個班級和6位老師的學(xué)校恢復(fù)了沉寂,曾經(jīng),很多“砍手黨”成員沒從這里畢業(yè)就外出打工,“以為搶完錢就跑了,根本不知道后面會發(fā)生什么”。
楊成康曾經(jīng)的兄弟、“砍手黨”的靈魂人物阿顯,被判刑15年,今年即將出獄,他曾把同鄉(xiāng)人的犯罪歸結(jié)于教育的落后和找不到工作、遭受歧視。
“請你們不要離棄他們。”面對前去拍攝的鏡頭,他把這句文縐縐的話念了好幾次,直至眼里涌出淚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