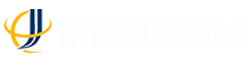文化沙龍主義-文化沙龍什么意思

《達達主義百年史》,作者:[德]馬丁·米特爾邁爾,譯者:史競舟,版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8月
一、個性的王袍:“達達”在造型設計中
1916年7月,當雨果·鮑爾想要在瓦格會館的舞臺上展現“個性之暴政”時,他已經用一種精心構筑的匪夷所思完成了這樣一種舉動,并且達到了近乎滑稽的程度。他將一套戲服套在了身上:
“我的雙腿被包在一個閃閃發亮的用藍色硬紙板卷成的圓筒里,圓筒高至臀部,這使我看上去就像是一座方尖碑;圓筒外面罩著一圈用硬紙板剪成的假領,內里猩紅,外表金黃,里外兩部分在脖子那塊相互連接,我可以通過抬放手肘讓它像翅膀那樣上下扇動;此外,我的頭上還戴著一頂藍白條紋相間的魔法師帽子。”
身著立體造型戲服的雨果·鮑爾。1916年攝于蘇黎世,拍攝者不詳,用作宣傳明信片,以為其在伏爾泰卡巴萊的演出招徠觀眾。
因為整個身體被卡在硬紙板卷成的圓筒里動彈不得,他只能被人抬著上下舞臺。這不僅與一個自我締造的暴君形象格格不入,而且看上去更像是一次拉下手剎的全速沖刺。一次在通往舞臺的第一道門檻那里就已亂了方寸的出場。雨果·鮑爾是否犯下了剛剛即位的暴君常犯的那種錯誤,即選擇了一套太過搶眼的充滿魔幻色彩的王袍,以至于這身裝扮以一種喧賓奪主的方式接管了暴君對自己身體的掌控權?
然而雨果·鮑爾既非暴君,也非標榜個性的吹鼓手。他低調內斂的性情,因善解人意而帶來的躊躇不決和出于正義感的審慎常引來朋友的交口稱贊。大張旗鼓地登臺亮相、當眾宣讀綱領并不是雨果·鮑爾的風格。因為生性靦腆,每次演出前他都要找個沒人的角落屏息靜氣一番,好讓自己緊繃的神經放松下來。他出場時的所有表現都印證了這種難度:再沒有誰會比他更缺乏自信和活力。或許這恰恰是雨果·鮑爾的宣言所要傳達的訊息?
暴君的耀武揚威不過是種虛張聲勢的表演,一個趔趄就能讓他的軟弱暴露無遺,因他自己并不清楚要把這威力用在何處?“這就是我!”——施蒂訥筆下的個人主義者高喊道。好吧。那么眼下又該怎么辦?身著戲服的雨果·鮑爾,是躍躍欲試卻又茫然無措的年青一代的偶像。自我解放、酒神精神或權力意志并不是這一輩人習以為常的功課。況且天賦的分配往往并不均衡,一個人對個性暴政的野心和可供其支配的表達手段之間很可能相去甚遠。
當一個人站在一覽無余的自由制高點上的時候,他面對的卻很可能是一個四分五裂的自我:“今天是社會主義者,明天是個人主義者,今天是徒,明天是無政府主義者。天哪,無數個聲音在我思緒萬千的腦海里一刻不停地喘息、呻吟、咆哮……我的耳朵快要爆炸了,那原本只是用來聆聽天籟的耳朵,那捕捉靈魂和詩意的聽覺容器。”(許爾森貝克)
雨果·鮑爾用他的立體造型戲服為全無實用性可言的奇裝異服樹立了一種標準,一種為日后的達達運動不遺余力地企圖超越的標準。當達達被帶到柏林之時,個性暴君的衣櫥里又多了一套閃亮耀眼的王袍:彼時,十一月革命遭遇了殘酷鎮壓,個體的行動力與個體自決也由此成為一個緊迫的政治議題。
二、收集世界:“達達”在拼貼藝術中
“光怪陸離的世界,當心!”格羅茨每時每刻都在收集手邊所能得到的一切,他的房間里貼滿了各式各樣的圖畫——假如啤酒或威士忌廣告,印著小丑、雜技演員和文身女人的馬戲團海報,或是照片和報刊上的插圖都能被稱為“圖畫”的話。一位青年藝術家馬克斯·恩斯特也對這種由視覺上的過度豐盈而引發的迷戀進行過描繪:“千差萬別的圖像元素匯集在一起,如此怪誕的堆砌在我內心引發了一種突如其來的視覺上的強化,從而喚起一連串令人目眩的矛盾圖像,并使它們變作兩倍、三倍,以至無窮……”紛然雜陳的元素成為一種日常體驗,挑戰著一切既有的藝術手法。怪異的視覺交響在人的內心深處久久回響。
一種可能的反應是對作為社會自身產物的“過剩”進行直接摹寫。這種摹寫談不上挑釁或批判,而僅僅是出于順應時代潮流的需要。格羅茨對這個過度豐饒的,蘊含著無限可能的世界有多熱愛,他對戰爭年代的柏林所呈現的那種丑陋就有多憎惡。早在大戰爆發前,格羅茨就已對生意人、有產者和市儈庸人的聒噪深惡痛絕。
戰爭則證實了他的厭世主義并非空穴來風。1917年他第二次應征入伍,在遭遇了嚴重的心理創傷后,他對紛繁世界的滿腔熱忱徹底轉變為辛辣的嘲諷,他開始向這世界展現其深不可測的黑暗。但怎樣才能恰如其分地呈現這種景象?怎樣才能以一種最直接的方式描繪“一塊塊裹在丑陋的灰布袋里的鮮紅肥肉坐在希亨啤酒館里胡吃海塞”的畫面?
《用達達餐刀剖開德國最后的魏瑪啤酒肚文化紀元》,漢娜·霍希。
為了找到理想的表現手法,格羅茨甚至臨摹過兒童涂鴉和公共男廁墻上特有的“風俗畫”。“漸漸地,我找到了一種像刀子一樣尖銳的風格,對于記錄我當時在一種厭世情緒支配下的觀察來說,這是必不可少的。”格羅茨回顧道。盡管很長一段時間里他一直靠畫漫畫維生并樂在其中,但他并不想止步于簡單的風格化,而是逐漸將自然研究作為一種修正和補充。
1917年,格羅茨與赫茨菲爾德兄弟開始了一段成果卓著的合作。他們共同致力于發現各種能夠恰如其分地表現當代性的藝術手段,還出版了豪華精美的大開本周刊《新青年》。可以清楚地看出,約翰·赫特菲爾德是如何把自己的版面設計實驗與格羅茨對駁雜現象的興趣結合在一起的。第5期上的廣告采用了版畫形式,在其中重復出現且交錯排列的特輯名稱已流露了幾分別出心裁的意味,第6期的整體版面設計在風格上則更為鮮明。赫特菲爾德采用的是一種刻意模糊了邊界的四欄式版面布局,反差強烈的字體、攝影、廣告欄、圖形元素和色彩在其中頻繁出現。翻開雜志,撲面而來的便是熨斗大廈的巨幅照片:一個力量與征服的象征,一份對美國文化的熱情告白,一場廣告的狂歡——熨斗大廈頂端斜貫一行字:廣告咨詢。
為了展現自己在廣告營銷方面的強大實力,雜志還特意采用了“格羅茨專輯商品目錄”這樣的封面標題。而尾頁上的廣告看上去則像是赫特菲爾德把一盒裝滿了火車頭、帆船、芭蕾舞演員、留聲機、小號、骷髏頭等各種花飾圖案的鉛字塊使勁搖晃一番后,信手撒在了尾頁的空白部分,接著又和必不可少的“新鮮出爐!”字樣連同二十幅石版畫的標題列在一處。位于中心的是整個版面上唯一一個被放大了的小圖標——骷髏頭,斜上方的禮帽使其看上去像是一位正在預告精彩節目的報幕員。相信任何一份達達主義出版物都會對這樣一種非常規的版式設計心領神會。
1920年達達博覽會某展廳內景,天花板處懸掛著長著豬頭的德國軍官。
凱斯勒伯爵則為赫特菲爾德與格羅茨第二階段的合作提供了契機。在他的安排下,赫特菲爾德和格羅茨入駐烏發電影公司(UFA),開始醞釀國家宣傳片制作事宜。之后,在他們的推動下,引領技術潮流的電影藝術正朝著用拼貼畫譜寫起源神話的方向奮力邁進。
三、《泉》:“達達”在風口浪尖
1917年,杜尚以一種離經叛道的挑釁方式迫使“排斥異端”的一幕重新上演:他將一只署名“R.Mutt”的小便器作為參展作品《泉》(Fountain)提交給第一屆美國獨立藝術家協會,而他本人也是協會的創始人之一。盡管杜尚匿名繳納了規定的6美元手續費,評委會卻對這件作品置之不理。“雖然我自己也是評審之一,但他們從未征求過我的意見,因為評委會不知道我就是那個作者。我之所以署名‘穆特’就是為了避免給這個作品留下任何個人印記。《泉》就那樣被他們草草丟在一塊隔板后面,整個展覽期間我都不知道它在哪里。我沒法振振有詞地說自己提交了那個東西。”
提交小便器的行為因開辟了先鋒主義藝術的先河而名聲大噪,其中一個原因便在于,杜尚通過這一手法揭示了無論評選還是不評選都是荒誕的這一事實。而同時性最終意味著,如實地展現整個世界在此時此刻的面貌,任何一個沒有被納入其中的平庸細節都會讓所謂的展覽變得毫無意義。
《泉》,馬賽爾·杜尚。
杜尚的小便器將傳統與反傳統、壓制與獨立之間的對立推向了極致,然而用“對立”一詞并不能對20世紀一二十年代形形的藝術思潮作出恰當的描述;它充其量只是為之開辟了一個空間。這樣的二元論很容易淪為僵化不變的陳詞濫調,因為驚世駭俗的東西總是容易傳播,且往往能給人以深刻印象。對巴黎沙龍評選流程的最初抗議就來自遭到詬病的體制內部。1863年沙龍的評審結果一經公布即引起了落選畫家們的強烈不滿,后者干脆創辦了一個“落選者沙龍”。落選者沙龍的引人注目之處恰恰來自一個悖論:它是正式展出的“異端”。
于是,在傳統和反傳統相互對立的表象之下,排斥與影響之間也形成了一種豐富多變、捉摸不定的關系。在諸如學院這樣遭到抵制的權威機構的空缺位置上,必須構造出新的網絡。現代派藝術通過追求獨立而贏得了屬于自己的公共空間。
但是,小便器對杜尚來說遠不只是一個挑釁,它和其他那些“現成品(Readymade)”——裝在凳子上的自行車輪,晾瓶架,或是一把被命名為“期待斷臂”的雪鏟,等等——一樣,無不遵循了“取消藝術家個人印記”這樣一種創作理念。與傳統油畫分道揚鑣的杜尚也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找到一種非個人化的繪畫形式:“徹底忘記自己的手,這就是我的觀念……當你畫畫的時候,無論你怎么做,你的個人喜好總是會摻雜其間。……我想找到一種擺脫傳統的東西……完全擺脫是不可能的,但我有意識地嘗試去這么做。我故意荒廢所學……我必須忘記自己的手。”
彼時,在歐洲大陸的工藝美術道路上,陶柏和阿爾普希望實現他們所向往的那種澄澈的形式和理想比例,并把來自外部的干擾降至最低,這種干擾主要來自藝術家本身——那個以其自詡高明、實則渺小的所謂“理性”不斷介入藝術創作的人。只有當藝術家的“手”無計可施,只有當他可以利用現成材料來完成“工作”,這一理想才可能實現。
就在阿爾普思考著如何排除藝術家的主觀意愿時,一個偶然的發現不期而至。有一次,因為屢屢無法達到預期的效果,他一氣之下把手中的碎紙撒落在地,這時他卻驚訝地發現,散落的紙屑竟然在不經意間拼出了他想要的圖案——至少漢斯·里希特是這樣描述的。散落在地上的紙屑,便是阿爾普的微型“伏爾泰卡巴萊”——鮑爾在創建卡巴萊劇場時運用的是同一種策略。偶然性成為藝術創作的關鍵要素,它通過取消藝術家而使藝術家的平衡技巧臻于完善。
四、真理之山:“達達”在世外桃源
1900年,幾個家境優渥的年輕人放棄了家人為他們規劃好的人生,決定一同脫離社會,結成一個屬于自己的聯盟。他們在阿斯科納的山上買下一塊地,開始了自給自足的農耕生活——“真理之山”部落就這樣誕生了。由于戰爭的關系,越來越多的另類運動團體選擇在阿斯科納扎營。這些墾殖地和定居點旨在開創一種新的道德和宗教,一種以集體勞動、土地與產品共有以及自由為基礎的全新社會形態,而這一社會形態也為人們所接受。
此時,雨果·鮑爾作為《伯爾尼才智報》的一名記者,在關于它們的報道中對其綱領及主張采取了十分友善的態度。在日記中,他還描寫了一個場面恢宏、令人嘆為觀止的大型舞蹈。由三部分組成的“太陽節”儀式在真理之山輝煌壯美的山景中拉開帷幕。一位朗誦者的身影出現在遠處的地平線上,身后即是正在墜落的太陽,他一面念誦著落日獻詞,一面向觀眾走來。此時,舞臺上架起的篝火被點燃,在繚繞升騰的煙霧中,群演如波濤一般涌動起伏。臨近午夜,觀眾被帶向山頂,演出的第二部分“”將在這里展開。精靈和女巫在一片周圍聳立著怪石巉巖的圓形草地上群魔亂舞,鬼影幢幢。在獻給日出的晨舞中,一群身著寬大絲袍的女演員涌向山坡。太陽自地平線上緩緩升起,霞光映照著舞者絢麗的衣衫。夜之邪靈被光明驅散,象征著白晝之星的永恒回歸的人潮開始歡欣涌動。第三部分名為“太陽的勝利”,在萬頭攢動中擔任領舞的蘇菲·陶柏作為火焰、精神和閃電的化身,引領著歡欣雀躍、翩然起舞的群演……
《誕生》,漢娜·霍希。
人應當成群結隊地脫離社會,在未被污染的大地上勞作耕耘,回歸真正的人性。“懷著對身陷迷途的人類的愛,懷著對我們的后代和對我們自己的愛,我們要徹底遠離人群,建立自己的生活和社交,用勞動創造來滿足生活所需。要盡可能地遠離國家,遠離商品和消費社會,遠離一切庸俗的生活!”古斯塔夫·蘭道爾如此向形單影只的少數派和離群索居的志愿者們發出呼告。工業化和理性主義催生了各種試圖在資本主義或共產主義之外另辟蹊徑的社會實踐。人類能否構建一種真正合乎理性的共處方式,而不是滿足于迅疾推進的工業化和狹隘的市民觀,滿足于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化或粗野的勞動贊歌?
對社會衛生狀況、食品供給和土地再分配的思考也催生了形形的社會改良理論和另類生活運動。1901年,詩人、出版商尤里烏斯·哈特和海因里希·哈特兄弟在柏林施拉赫滕湖畔創立了“新社區共同體”。推動這些社會運動的并不是階級斗爭,而更多的是一種將分崩離析的現代世界重新統一起來的愿望:“新社區共同體旨在通過宗教、藝術、知識和生活的融合來實現個體與社會之完善這一人類理想。”位于德累斯頓赫勒瑙的“城市花園運動”則是另一個以合作社形式來抵御都市生活所帶來的各種弊病和肆無忌憚的地產開發的社會實踐案例。
《斷念》,漢娜·霍希。
蘭道爾倡導的“遁世者聯盟”試圖將一種對社會的失望情緒引向神秘主義。作為一名徹底的社會主義者,蘭道爾的目標是社會財富的平均分配:“現實中有一種情況屢見不鮮,那就是很多人雖然參與創造了經濟價值卻仍然一貧如洗,而那些沒有參與社會勞動或無所事事的人卻可以坐享其成乃至發家致富;還有很多人盡管抱有勞動的意愿卻不被允許從事勞動。”
但所有這些改造社會的努力無不以一種深厚的人文主義傳統為背景,也因此而與大多數社會主義思潮所宣揚的唯物主義價值觀格格不入。努力維系世界的完整性,以免其在現代性的沖擊下分崩離析,這是一種多余的愿望。因為在蘭道爾看來,無論世界還是人類自身都仍然是一個相互聯結的統一體:一個被現代社會的世俗化表象所遮蔽的人類共同體。所有自命為個體的現代人,都只是一個宏大整體的“表象、節點和火花,是那種可以被稱為人類、物種或宇宙的心流(Seelenstrom)的驟然閃現”,而現代社會標榜的個人主義卻阻礙著人類走向這一宏大整體。在他所處的時代,蘭道爾看不到任何與“心流”連通的路徑,人們誤入迷途,沉溺于一個個微不足道的“小我”。這將是一段充滿艱辛的崎嶇之旅,因為只有取消“小我”才能成就一個擁抱世界的“大我”,也只有到那時人們才會看到一個美麗新世界。“讓我們拭目以待,看我們將如何成為上帝,如何從我們自身之中發現整個世界的存在。”
原作者丨[德]馬丁·米特爾邁爾
摘編丨肖舒妍
編輯丨張進
導語校對丨 陳荻雁